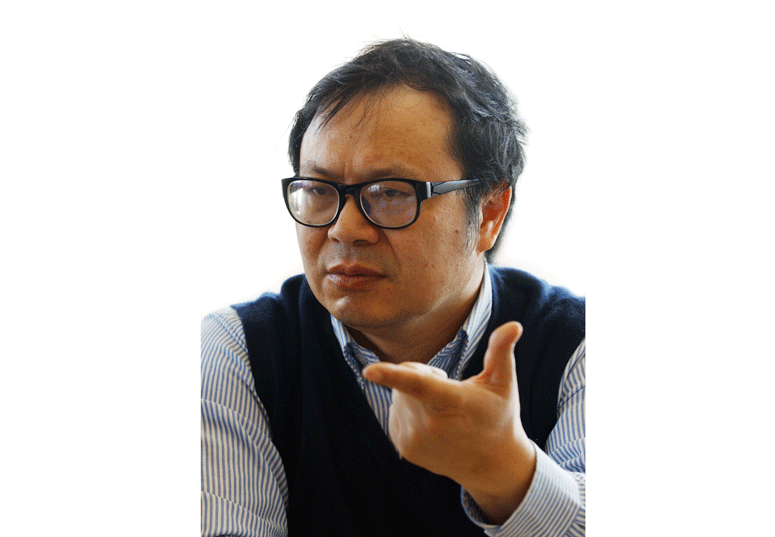15世紀(jì)至18世紀(jì)之間,各種文化屬性構(gòu)成的一種新文化聚合體,在歐洲出現(xiàn)了。因而,歐洲的城市生活,從形式到內(nèi)容,都發(fā)生了巨大改變。當(dāng)時的社會生活新形勢,是從幾種新要素中產(chǎn)生出來的:一種新的經(jīng)濟(jì)模式,就是資本主義的重商主義;第二個就是新的政治框架,主要就是中央集權(quán)專制制度,或者說君主寡頭政治,而且,往往是以國家形式出現(xiàn);再一個,就是新型的意識形態(tài),也就是衍生自經(jīng)典機(jī)械物理學(xué),只不過其中潛在的許多基本原理,其實早在古代軍隊和修道院時期就已形成了。
不過直至17世紀(jì)以前,這些發(fā)展變化還是混沌不清的、猶豫不決的,且僅出現(xiàn)在少數(shù)地區(qū),只在局部領(lǐng)域顯現(xiàn)成效。而從17世紀(jì)開始,上述各要素開始聚焦,圖像突然明朗化。到這一步,中世紀(jì)的秩序,純粹因為自身內(nèi)部的腐敗,而開始分崩瓦解。緊接著,宗教、貿(mào)易、政治開始分道揚鑣,各奔前程了。
要了解歐洲中世紀(jì)以后的(post medieval)城鎮(zhèn)社會,有種仍然時髦的說法,我們就必須十分警覺:這種說法夸贊文藝復(fù)興,稱它為一個偉大的運動,引領(lǐng)人類走向自由,重新建立了人的尊嚴(yán)……。原因在于,歐洲文化的真正復(fù)興運動,以及城鎮(zhèn)建設(shè)和思想大發(fā)展的偉大時代,早自12世紀(jì)就已經(jīng)開始,并且在一系列學(xué)者和作家作品中留下了里程碑式的禮贊,這些學(xué)者和作家包括:13世紀(jì)的意大利神學(xué)家托馬斯·阿奎那;德國哲學(xué)家,阿奎那之師,圣亞伯特·馬格魯(Saint Albettus Magnus,1193—1280年);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詩人但丁,以及意大利著名畫家喬托”。就在那次文化復(fù)興和15世紀(jì)文藝復(fù)興之間,14世紀(jì)歐洲發(fā)生了一次浩大的自然災(zāi)難:黑死病。根據(jù)最保守的估計,死亡人數(shù)在總?cè)丝诘娜种恢烈话胫g。到了16世紀(jì)時,所遭受的損失雖然已經(jīng)復(fù)原;但這場瘟疫所造成的社會文化斷裂,卻隨地方社區(qū)活力的下降而雪上加霜,正如每一次長期消耗戰(zhàn)爭之后的情形一樣。
在接踵而至的社會解體過程中,掌控著軍隊、貿(mào)易通道、巨額資本積累的人,自然也就掌控了社會權(quán)力。隨著軍事獨裁 主義興起,開始鎮(zhèn)壓大學(xué)里的學(xué)術(shù)自由傳統(tǒng),而且為了維護(hù)世俗統(tǒng)治者的利益,也開始鎮(zhèn)壓神權(quán)領(lǐng)域的獨立自主精神。凡此種種,都仍然可以從現(xiàn)今世界聽到回聲:幾乎與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之后俄國、德國、意大利,以及歐洲其他一些地區(qū)所發(fā)生的情形差不多。而且,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之后緊接著發(fā)生的情況也很類似,即使美國與歐洲在地理上相距甚為遙遠(yuǎn)。與此同時,大學(xué)從原來的學(xué)者們的國際性聯(lián)合體蛻變?yōu)槊褡逯髁x組織,屈從于新型暴君,抵制所謂“危險思想”,用效忠誓言束縛人的行為和言論自由,這樣的進(jìn)程,不僅在學(xué)術(shù)機(jī)構(gòu)——大學(xué)里穩(wěn)步進(jìn)行著,而且在教會和城市神會里,也照樣辦理。
就這樣,僅僅經(jīng)過了幾個世紀(jì),中世紀(jì)一些十分古老的組織制度和社會慣例,都顯現(xiàn)出道德敗壞的跡象。荷蘭著名歷史學(xué)家赫伊津哈‘在其《中世紀(jì)的消亡》(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)一書中,曾經(jīng)以豐富的實例記述了這個深刻的社會變遷歷程。根據(jù)馮·貝婁(George Anton Hugo yon Below)的研究成果,15世紀(jì)的時候,開始了有組織的賭博活動,賭博場所的房屋居然是由市政當(dāng)局提供的。教會也有同樣的傾向,不僅買賣官職,也出售賜福,而且迷信活動再次廣泛恢復(fù)。巫師巫術(shù)活動,早在8世紀(jì)就曾被圣龐尼菲斯(Saint Boniface)禁止了,此時卻大行其道,直至1484年被教會正式認(rèn)可;其原因可能是此前已經(jīng)存在著異教徒祭拜土地的活動,這些都有悖于基督教的道德戒律。而且,到了17世紀(jì),以自然科學(xué)的精確研究和度量方法的出現(xiàn)為標(biāo)志,懲罰和迫害巫師的事情就開始流傳開去。而這其中一些最著名的受害者,往往就是新型的科學(xué)家和哲學(xué)家;比如,像英國哲學(xué)家、作家兼教士的約瑟夫·格蘭維爾這樣的思想家,他們都幾乎同時預(yù)言了,未來的時代里,科學(xué)技術(shù)即將徹底改變?nèi)祟愇镔|(zhì)世界。
但是,黑死病所帶來的驚惶,也產(chǎn)生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反響:人們花費極大的努力,不是去對付死亡,爭取永生、安全、穩(wěn)定,而是瞄準(zhǔn)了世俗人生中能夠獲得或者掌握的一切。于是乎,七大不可饒恕的罪惡當(dāng)中,一夜之間,競有六項變成了時髦的美德,而且,其大罪惡當(dāng)中第一項,驕傲,竟然成為了社會的領(lǐng)袖人物們特有的品質(zhì),無論是賬房里的,還是戰(zhàn)場上的領(lǐng)袖人物。生產(chǎn)財富、展示財富、奪取權(quán)力、擴(kuò)張權(quán)力,變成普遍的欲求和要務(wù)。本來,以往的社會好久以來也是這樣做的,但是,如今卻成為全社會公開的指導(dǎo)原則了。
從中世紀(jì)的包羅萬象(medieval universality)過渡到巴洛克的千篇一律(baroque uniformity),從中世紀(jì)的地方保護(hù)主義過渡到巴洛克的中央集權(quán)體制,從中世紀(jì)時代上帝和神圣天主教教會的絕對權(quán)威過渡到世俗行政管轄和民族國家的絕對權(quán)威……這一組組對偶的兩者,既是權(quán)威又都是民眾集體崇拜的對象;而兩者間過渡階段的完成,經(jīng)歷了大約4個到5個世紀(jì)之久,才最終實現(xiàn)了舊的機(jī)構(gòu)制度向新型機(jī)構(gòu)制度的轉(zhuǎn)換。我們不必單單稱頌這一時期光鮮的方面,而諱言這一社會變動過程中最根本的實質(zhì)問題。中世紀(jì)里,古典世界偉大遺物的重見天日和重新評價,柏拉圖和維特魯威的被發(fā)現(xiàn),建筑學(xué)里恢復(fù)五種柱式的顯赫地位,古董裝飾所帶來的感官快樂,以及紛紛建立起來的一些人物雕像……凡此種種,都給巴洛克統(tǒng)治權(quán)力的暴政和恣縱蒙上一層頗有美學(xué)意味的外衣。像西普里多·維特萊斯科(Hippolito Vitellesco)那樣的鑒賞家,也許會去擁抱人物雕像,將其當(dāng)作活人一樣與之對話(根據(jù)約翰·伊芙林報道);然而,真正的活人卻被巴洛克變成了機(jī)器,沒有思想,只服從外來命令,儼然就是以皇帝為中心的古代城市的死灰復(fù)燃。
這些新秩序后面潛藏著的趨向,直至17世紀(jì)才顯露出來。而且,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開始背離中世紀(jì)樞軸,并逐步在新徽志下重新形成社會組合,這個徽志就是君主。意大利政治家馬基雅維利(Machiavelli,1469—1527年)主張實現(xiàn)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,這個政治家在其《君主論》(Prince)一書中,就為巴洛克新政治和新城鎮(zhèn)的規(guī)劃提供了不少線索;此外,后來出現(xiàn)的笛卡兒,也按照巴洛克城市的統(tǒng)一樣式,重新解釋了科學(xué)技術(shù)時代即將出現(xiàn)的新世界。總之,到17世紀(jì)時,當(dāng)時思想界的先驅(qū)人物,如阿爾伯蒂等人,他們的一些直覺和設(shè)想,通過巴洛克的生活方式、巴洛克規(guī)劃、巴洛克花園、巴洛克城市,都一一實現(xiàn)了。